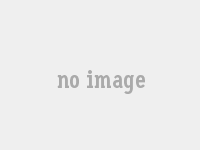老旧儿童照片大全(儿童成长档案爱护环境图片老照片里的儿童福利和儿童救济记忆)
少年儿童朝气蓬勃,是党和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从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战略高度关心重视少年儿童。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总是悉心关怀爱护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今天,一起通过老照片,回顾那些关于儿童福利和儿童救济的故事。
三千孤儿入内蒙:
接一个 活一个 壮一个

当年的都贵玛与孩子们。

牧民与“国家的孩子”。
6月1日前夕,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基地迎来了众多参观群众。他们带着孩子,随着讲解员的脚步,认真观看“人民楷模”都贵玛的荣誉奖章、勋章、手写的入党誓词、用过的药箱等珍贵物件、老照片。“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感人故事也在讲解员的舒缓语调中徐徐展开。
时光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那会儿,我国遭遇罕见的自然灾害,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孤儿院涌入大量嗷嗷待哺的幼儿。党和政府决定,把这些孩子送到草原,由牧民抚养。周恩来总理一再叮嘱:“要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安排好!”
内蒙古自治区时任主席乌兰夫向党中央郑重承诺: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份泛黄的档案记录,纸上真实地记录着1960年上海孤儿入内蒙古的历史:6月,呼和浩特组成17人赴上海接运组,接运100名孤儿;7月,伊克昭,19人接运小组出发,接运100名孤儿;8月,哲里木,17人接运小组赴上海,接运60名孤儿……
在“1960年移入儿童设备购置费明细表”中,有小木床、小毯子、小桌子、便盆、澡盆、枕头……以及4500块尿布。
从1960年到1963年,3000多名孤儿坐上一列列火车,跨越山河,一路向北,到了遥远的内蒙古大草原。他们中最大的七岁,最小的只有几个月。
得到消息后,草原上的农牧民们争先恐后地来了,有的骑着马,有的赶着“勒勒车”,到育儿院申请领养孤儿。这些被称作“国家的孩子”的孤儿,相继被11个盟市、37个旗县的千余个家庭收养,从此他们有了新的家、新的“额吉”(蒙语:妈妈)。
资料显示,1960年,乌兰察布盟(现乌兰察布市)接收了92名孤儿。他们当中的28名来到四子王旗。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的牧民都贵玛当时年仅19岁,由于念过书、做事认真,被选到四子王旗保育院当保育员。
据四子王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当时的旗保育院设在乌兰花镇,孩子们在旗保育院休整了4个月后,都贵玛便独自一人带着这28个孩子回到了脑木更苏木保育院的蒙古包中。
谈及自己第一次见到孩子们的情景,都贵玛老人回忆道,因为自己没当过母亲,所以年龄最小的孩子叫出第一声“额吉”的时候,她的脸“腾”的一下红了。
在蒙古包里,都贵玛把孩子们的床摆成圆形,自己睡在中间,这样晚上不论哪个孩子哭醒,她都能以最快的速度照料他们。就这样,一年多里她没睡过一个完整觉。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照料,原本瘦弱的孩子们逐渐适应了草原的环境,茁壮成长。当地牧民家庭也开始陆续收养这些孤儿。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些“国家的孩子”在草原上扎下了根。长大后,他们有的成了牧民,有的成了医生、教师,还有的成了高级工程师、公务员……如今,他们也都年过六十。
大爱无疆,一直以来,以都贵玛老人和28个孩子的故事为代表的“三千孤儿入内蒙”佳话在歌声中传扬、在荧幕上重现、被写进书中。2019年,都贵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以及中宣部表彰的“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专门讲到了“三千孤儿入内蒙”这段历史佳话。
历史不会忘记,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生活并不宽裕的内蒙古牧民们,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3000多名嗷嗷待哺的汉族孤儿,这是历史的丰碑,更是一场爱的传递。(来源:新华社、《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基地等。)
上海儿童福利站:
把最宝贵的东西给儿童

宋庆龄在上海儿童福利站教孩子们识字。

“小先生”教孩子们唱歌。
上海解放前,当地许多儿童在战乱和贫困中挣扎,缺衣少食,没有机会接受教育。1946年至1947年期间,宋庆龄带领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贫苦儿童聚居的地区先后创办了三个儿童福利站,开展救济和教育儿童工作,后来被统称为上海儿童福利站。福利站不仅帮助了贫苦失学儿童,还培养了一批青少年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
1946年10月12日,中国福利基金会首先在沪西胶州路725号晋元小学内创办了儿童图书阅览室。
1947年4月4日,在阅览室基础上扩充建立第一儿童福利站,站内设有图书阅览室和保健室,免费向贫苦失学儿童开放,为贫苦民众治病。
“铁皮房子十尺宽,好似狭长一旱船。旱船前舱是教室,后舱还要摆图书。黑漆门儿朝东开,一片阳光进屋来。你也来,我也来,来读书,来唱歌。”就是这么一个很简易的小天地,却成为当时贫苦儿童的“快乐家园”。
宋庆龄还将教育家陶行知所倡导的“小先生”制引进福利站,由附近公立学校的学生担任教书先生。当时,福利站的老师绝大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组织教书的学生学文化、学时事,阅读进步书刊,唱革命歌,演进步戏,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由此培养出了一批“小先生”。然后,再让这些“小先生”带着小黑板走街串巷,教授更多儿童识字,唱诵进步歌曲,传播革命思想。
第一儿童福利站第一任站长马崇儒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是“小先生”活动的拥护者。当时的第一儿童福利站除了为贫苦失学儿童开设扫盲识字班之外,还在沪西工人区的一些街道开辟家庭、里弄、棚户识字班。第一儿童福利站周围的金科、晋元、华模、南屏中学品学兼优的学生都曾担任过“小先生”,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帮助贫苦失学儿童扫盲。识字班的教材是第一儿童福利站自编的《老少通》识字课本,既适合不同年龄的儿童,也可以供成人学习,内容包含语文、四则运算、珠算和记账等。
1947年10月、11月,宋庆龄又带领中国福利基金会相继在沪东许昌路811号、虹口乍浦路245号建立了第二、第三儿童福利站。至1949年5月,三个福利站共培养出170位“小先生”,开办了数百个识字班,受教儿童达5000多名。上海儿童福利站,成为战乱中贫困儿童的“诺亚方舟”,庇护他们学习、成长。
那个时期,上海儿童福利站还负责把中国福利基金会募捐的物资,发放给贫苦儿童及其家庭。1948年春,新闸路金家巷发生大火,1800多名居民无家可归。当时的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无从顾及。第一儿童福利站立即向中华救济团申请到1.8万斤救济米。福利站组织“小先生”在3天时间内完成了金家巷灾民的访问、登记和救济米发放工作,缓解了灾民的燃眉之急。
1949年春,上海陷于极度混乱。出于人员安全考虑,上海儿童福利站暂停了白天的活动。晚上,“小先生”们来到福利站制作欢迎标语,缝制彩带。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时,上海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们是最早出现在街头的一支队伍,孩子们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迎接上海解放。
1950年2月,三所儿童福利站分别改组为妇幼保健站、少年儿童文化站和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儿童福利站的工作随之结束。(来源: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解放日报》、《上海市重要革命遗址通览》等。)
延安保育院:
亦有星星火 作歌靠少年

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大门。

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孩子们合影。
延安保育院是设立在延安的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中央托儿所、陕甘宁边区第二保育院等保育机构的统称。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到达延安后至抗战胜利,延安保育院共养育了近3000个孩子。
“儿童万岁”
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延安。3月,在延安城南的柳林村办起了延安托儿所,接纳了18名前方将士子女和烈士遗孤婴孩。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侵华日军的铁蹄蹂躏下,无数儿童饱受战争摧残。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提出在延安托儿所的基础上扩充建立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由中央医院护士丑子冈负责主持扩建事务。1938年10月2日,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正式成立,不但收容烈士遗孤、前线将士和革命干部子女,还接纳无家可归的难童。毛泽东为第一保育院成立亲笔题词“儿童万岁”。
第一保育院成立初期,只有婴儿部和幼稚部,共有幼儿57名、工作人员19名。虽然人数不多,但柳林村院址房屋狭小,已经不敷使用。再加上这时候日军占领了临汾机场,为了防止日军空袭,1938年11月10日,第一保育院从柳林村迁到安塞县小草峪村。
小草峪村虽然隐蔽安全,但地势狭小,环境闭塞,随着入院儿童的不断增加,这里的院址很快也不够用了。于是,边区政府和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筹资在延安避风向阳的李家洼修建保育院新址。1940年秋,新院址建成,第一保育院在建院两周年之际搬回了延安。
这时的第一保育院,接纳了300多个儿童,工作人员增加到120名,并发展到乳儿部、婴儿部、幼稚部、小学部的细分建制。不但在延安,在当时中国的幼儿保育机构中也是规模比较大的。
1940年,在距离中央驻地杨家岭很近的兰家坪,还建起了延安中央托儿所,由曾经主持扩建第一保育院的丑子冈任所长。
1944年秋,为解决出征干部子女的寄托问题及烈士子女的抚育问题,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商定,由康克清牵头筹建陕甘宁边区第二保育院,并于1945年6月建成。
“不能死孩子”
第二保育院的首批孩子,最大的6岁多,最小的才1岁,其中还有一名麻疹潜伏期的孩子。
很快,麻疹就如暴风骤雨似的向第二保育院袭来,全院的孩子一下子都感染上了,病情严重的还并发了肺炎、肠胃炎等。
即使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这样的疫情也属危急,更何况延安当时正处封锁之下,缺医少药。第二保育院建院的第一个目标,居然成了“不能死孩子”。
陕北地区水资源匮乏,为了改善卫生条件,让孩子们使用流动的净水洗手,保育员特别制作了用于洗手的木桶;让孩子们每天有充足的时间享受黄土高原上的“日光浴”,消毒杀菌;准备了两口大锅,24小时沸腾,孩子的碗筷、用品,全都扔进去煮。党中央还通过办事处负责人,为孩子们买来几十头奶牛用于补充营养。
这场麻疹疫情持续了70多天,在第二保育院全体人员的努力下,近60名感染麻疹的孩子全部康复,无一夭折,堪称奇迹。
有了这次经验,第二保育院设立了健康测验检查制度,并在延安保育院推广开来。每半月进行一次五官检查,每季度进行一次全身检查,每年注射一次霍乱、伤寒疫苗,隔年接种一次牛痘疫苗。
“娃娃长征”
1946年11月,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从延安转移。
小驮床就是那个时期的发明,它类似于驮筐,拴在骡马背上一边一个,造型上则是一个护栏很高的婴儿床或者摇篮。后来人们常用“马背摇篮”比喻延安保育院,即由此而来。
当时,第一保育院、中央托儿所和第二保育院并没有一起行军,撤离路线也不尽相同,但三支队伍面临的几乎是同样的艰难险阻。
每个阿姨照看三四个孩子,大的不过六七岁、小的还在蹒跚学步。孩子长途行军,除却翻山越岭的艰辛,还要防备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敌机的狂轰滥炸,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疾病,可谓困难重重。
那时,队伍白天休息、晚上赶路,不走大道,风雨无阻。经过两年多的艰苦行军,三支队伍终于安全到达解放区。延安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保护孩子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在”的誓言,创造了数千里行军的“娃娃长征”没有一个孩子掉队、没有一个孩子伤亡的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分别落脚北京、西安和延安三地,发展成为现在的北京育才学校、西安市第一保育院、西安市育才中学、延安育才学校。中央托儿所和第二保育院则跟随党中央到了北京,分别是现在的总政幼儿园和北京六一幼儿园。
在某种意义上,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是抗日救亡洪流中幸存下来的幼小生命,也是中国革命的小火种。而延安保育院保存了燎原的星火,积蓄起永续发展的力量。(来源:《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侠客岛、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等。)
整理:《中国社会报》记者赵晓明、张路曦、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