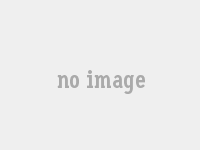世说新语中的小孩都有谁(古文中爱护儿童的《世说新语》中的儿童形象特点及其成因)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中成就最高的著作,全书涵盖了各色人物,其中又有上百则与儿童相关。童年作为人的知识和品格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人生有着重要影响。因此,通过《世说新语》中儿童形象的探究,我们能更加了解魏晋文人的思想态度和人生追求。
一.《世说新语》中的儿童形象特点
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应该是其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所展现出来的形象的集合,童年、中年、老年,每一个阶段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因此,将其在不同阶段展现出来的特点进行整合概括,方能看到一个愈加全面而真实的人物。俗语说:“三岁看老”《世说新语》中出现的那群风流名士究竟是如何造就的,或许从其童年时期我们就可略见一斑。
1. 1敏于辞令,聪慧机智
《世说新语》中儿童的言辞极有特色,通常在简短的对话中就显示出其良好的素养以及超凡的气质。在《言语》(二)中,孔融十岁时随父拜见名士李膺,被问和李家是何亲戚时,他回答道:‘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仅仅十岁便说出这般惊人之语。而一宾客却嘲讽他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反驳说‘想君小时,必当了了!”这正是采纳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巧妙地回击了客人的嘲讽。
拥有高超的论辩才能成为当时儿童的一大特点,这其实与当时清谈之风盛行密切相关。鲁迅先生认为:“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在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尚清谈,而清谈者多具有较强的论辩能力,儿童们耳濡目染中也逐渐学会了思辨。在《言语》中,徐孺子在月光下独自玩耍,当被人问及倘若月中无一物时还会如此明象吗,年仅九岁的徐孺子回答说:“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事物正是在相互之间的对比衬托下才愈发地显现其特色,月亮也是如此,此番言论己与清谈无异,较之成年人毫不逊色。这些孩子言语中透露出来的哲理色彩正是受到成人社会盛行清谈之风的影响而出现的。
1. 2品德方正,为人理性
自东汉末,尽管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多元化倾向,使儒家地位受到极大冲击,但“根深蒂固的理性思想并未完全丧失对人的控制力量”,儒家学说在规范着人们的言行和举止、社会稳定方面依旧发挥着重大作用。由此可见“儒家的经典教义的确己内化到少年儿童幼小的心灵中,变成了个体的内心信念”。
《世说新语》中的这群儿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故而具有美好的品德,他们生性善良,富有同情心。在《德行》(三三)中提到谢安年少时,遇其兄谢弈惩罚一位触犯刑法的老翁,以至于“乃至过醉,而犹未己”,心有不忍,便向兄长求情。虽然老翁犯错,仍不忍过多苛责,由此看出谢安作为孩童特有的天真善良,这也是儒家仁义观念的显现。
受儒家思想影响,这群儿童还具有正确的道德观和强烈的家族观念,明辨是非,尊儒守礼。如《方正》(一)中,元方之父与友人约定日中出行,友人姗姗来迟,来时却只见元方在门外玩耍,愤怒之下说出“非人哉”,年仅七岁的元方立即反驳说:“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陈元方虽是七岁稚童,却用儒家的种种行为准则来评判是非,由此便可看出魏晋时期的儿童在传统的儒学的教育下,具备了家族观和道德观,善辩是非。
在《德行》(三八)中,范宣八岁时,在后院挖菜,误伤手指,啼哭不止。然而被问及“痛耶?”范宣却回答说:“非为痛,身体发肤,不能毁伤,是以啼耳。”因为损伤了授之于父母的身体发肤而哭泣,一个八岁孩童说出如此话来,不能不让人感叹其成熟和理性。
1. 3学识渊博,个性张扬
《世说新语》中的儿童大多学识渊博,这与当时的家学教育分不凡《世说新语》中的少年多出身士门大族,这些家族为维护自身家族利益,加强对子弟的培养。同时文学在此时高度发展,受到普遍关注,因此出身于名士大族的子弟多具深厚的文学修养《言语》(四六)记载谢尚八岁时随父亲送客,虽然年幼,但谈吐举止己可圈可点,众人称赞他是颜回,谢尚随即回答“坐无尼父,焉别颜回”。既是对众人的称赞,又是对于自己的肯定。如若胸无点墨,又岂能说出这般妙语。正是由于谢尚虽年幼却己具有丰富学识,才能如此作答。
罗宗强先生说:“随着经学束缚的解除,正统观念的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个性张扬这点大异于其它时代,儒家历来讲究谦逊有礼,但由于在魏晋时期受到了挑战,其权威下降,再加上玄学等其他思想的兴盛,使得在此时的士人追求自我,张扬个性。在《言语》(八九)中写到,晋简文帝逝世,孝武帝当时年仅十几岁便立为新皇,直到傍晚,他都不去哀哭。左右侍从都劝他应当按常理去哭吊,孝武帝回答说:“哀至则哭,何常之有?”人哀痛到极点自然便会痛哭,何必依常理?遵循自己内心的意愿行事,敢于打破常规,不在乎世俗眼光,个性的张扬表现得淋漓尽致。
《世说新语》中的名士在其儿童时期便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聪慧机智,通过对他们儿童形象的研究,能更清晰地了解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追求和生活态度。
二.儿童性格形成原因
2.1社会文化状况
魏晋时期,南北分裂,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矛盾重重。《晋书·阮籍传》中写到:“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动荡的局面使下层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正是对该时代满目疮咦、哀鸿遍野景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不幸的时代,到处充斥着战乱、饥荒和疾病,然而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各种思想彼此交融、碰撞,创造了魏晋时期的文明。透过这群儿童,便可以看出该时期的文化状况。
鲁迅在《吃教》中曾说道:“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洁经》。”其中《论语》和《孝经》实指儒学经典,由此可知,儒学传统的作用仍旧不可替化《颜氏家训·勉学》中提及:“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惟》,少者不失《诗》、《论》。学习儒家经典在此时仍是一种社会风气。以《诗经》为例,由于《诗经》在魏晋士人间广为流传,以至于儿童也对《诗经》中的内容耳熟能详,并将其运用到日常交际中。如,一次孙放随父打猎遇到庆亮,庆亮玩笑道:“君亦复来邪?”孙放回答说:“无小无大,从公于迈"《诗经·鲁颂·拌水》)一语双关,意味深远。其次,儒家提倡的忠孝仁义等观念己深入人心。范宣深受其影响故而爱惜身体。陈元方为保父亲名誉与大人据理论争,正是由于忠孝观念和家族观念在他脑中己根深蒂固。谢安极有仁义观念故而不忍老翁受罚。种种事例表明们比说新语》中的儿童具有品德方正的特点正是儒学作用的结果。由此可知,儒学在此时,尽管其曾有的独尊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但儒学的政治统治地位却并未动摇,依旧维持着其宗主地位。
玄学是该时代主要的哲学思潮,其兴盛有力地冲击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思想。卜宪群曾说过:“玄学以自然放任思想,猛烈抨击乃至全面否定儒家的礼乐名教。”[0]玄学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但儒家思想在伦理道德观念方面力量强大,而要任自然、重情性,就势必要与名教观念发生冲突。稽康对此的态度很坚决,他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完全否定名教。但是多数文人却将名教与自然引为一体,可谓是“虽有玄思,虽向往自然任心,但不违反名教”走上了玄礼双修之路。谈玄在当时己蔚然成风,是否精于谈玄己成为评价名士的重要标准。许多高门大族既是儒宗,又是玄学家族。正是兴盛的玄学培养了儿童的内在逻辑性和言语表达能力,使他们巧于言辞,极具思辨能力。如,元帝问明帝长安和太阳相较哪个更远,小小的明帝回答说是太阳远,因为“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然而次日再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他认为比起太阳,长安更远,其回答与上次截然不同,因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哲学的思辨色彩己是相当浓郁。
魏晋时期,佛教的发展极为兴盛,其推崇因果报应的“三生”论,既为统治者提供了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教导他们及时行善得善果,又给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带来生存的希望,迎合了时代需求。玄学讲究“无”,佛教讲究“空”,两者旨趣相投,彼此融合,最终走向了玄释合流之路。张玄之和顾敷随祖父顾和去佛庙里,见佛像表情造型均不同,有的哭泣,有的微笑。对于这种情景,顾敷认为是“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抛开世俗情感故能坦然自若,忘不掉人世感情故而留恋垂泪,顾敷巧妙地融佛理于玄言之中。体现出此时的儿童受多种思想影响,思维活跃。当然,除却上述的思想以外,魏晋时期的其他思想在此时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顾明远曾总结此时的思想为“儒学独霸舞台的状况被打破,形成了儒、佛、道、玄、文、史、名法多元并存和争鸣互黝的局面”。正是由于此时思想融合,才使得《世说新语》中的儿童具有敏于言辞、善于谈玄、知识渊博的特点。
2. 2教育方面
魏晋时期,官学时废时兴,己无力承担主要的教育职责,对于儿童的教育主要通过家族的私学展开,而究其原因则是为了“芝兰玉树生阶庭”。
一是,文化教育。文化在巩固家族地位中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文化教育往往与家族教育结合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甚至可以说,文化教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族教育彰显其功用。魏晋时期,由于世家大族在诸多方面占绝对优势,使得“学术文化活动呈现两个特点:家族化和地域化”。钱穆在《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曾写道:‘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可见在此时的诸多高门士族通过传承文化来保持自身家族的昌盛不衰。
魏晋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加之这些高门大族也非常重视培养子弟的文学修养。因此出现了文学世家,其特色就是以文学相传。在《言语》(七一)中,谢安与亲友在下雪天相聚一起谈诗论文,当雪下得紧时,便欣然问道:“白雪纷纷何所似?”侄子谢朗回答说‘撒盐空中差可拟。”侄女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于是谢安大悦。从这件小事中便可看出文学在此时己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情感生活的组成部分,而魏晋文人对于文学的重视也由此可见。同时,文学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提高了人们的文学修养,丰富了文人的知识储备,而且有助于健全人格,培养气度。
二是,人格教育。人格教育也是世家大族教育子弟的重要内容。受玄学文化的影响,魏晋名士多提倡自然主义的教育方法《德行》(三六)中,谢安说:“我常自教儿。”即是遵循了道家“行不言之教”的思想,使子弟在耳濡目染中培养自身品格。《雅量》(六)中,庆亮风度仪表均壮美优雅,时人对此表示怀疑。其长子阿恭年方几岁,气质便高雅稳重,神似其父。温娇曾躲在帷幕后面去吓他,这孩子神色安然,缓缓地跪下来问对方为何如此。由此可以看出魏晋名士多风度雅然,也是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养成的。
由于信奉自然主义教育方法使得魏晋名士在教育孩子时,注重在尊重和关爱中培养孩子的人格。针对孩子的特点,主要采取以鼓励引导为主的方针,营造较为自由开放的教育环境,这种环境益于开发儿童智力,便于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活跃他们的思维。谢玄少年时喜欢紫罗香囊及手巾之类的东西,谢安忧虑,“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假谲》(十四))谢安出于对孩子的关爱,就以打赌的方式来纠正谢玄的不良嗜好,这样既能尊重孩子的人格,又可保护他的感情和自尊。
谢安曾问自己的后辈,为什么要使家族子弟他们美好呢?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言语》(九二))这句话其实就揭示了此时教育的最终归宿—芝兰玉树生阶庭。
总之《世说新语》中的儿童群像历经千年仍旧闪耀文坛,这些儿童最富代表性和最具时代特色的行为特点和个性特征,也为我们理解魏晋风度和社会风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